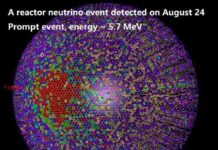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7月25日電 題:數字技術如何賦能環境權益保護?
作者 鈄曉東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多年來,中國環保領域運用數字技術的速度顯著加快。翻看環保板塊上市公司年報,“智慧運營”“數字化管理”等已成為高頻詞,反映出中國環境保護與數字化的融合早已不是紙上談兵或簡單的概念叠加,而是藉助規範適配與數字技術嵌入,推動環境權益保護的多樣化發展。這種融合既體現了數字技術對環境權益保護的加持,也反映出環境法律制度對數字技術應用的規範。
數字技術重塑了環境保護的方式和場景,給環境權益保護帶來了新變化,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五個關鍵方面。
首先,量化環保目標,提昇感知能力。藉助衛星、物聯網等組成的“空天地一體化”監測網絡,數字技術能把生態文明的“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等抽象要求,轉化為看得見、可追溯的數據指標。
例如,全國生態環境智慧監測平台連接了系列物聯網監測點和遙感衛星數據,實現對空氣(如PM2.5)、水質(地表水Ⅲ類以上水體)等關鍵指標的實時監測,將數據更新頻率調整為分鐘級。隨著監測技術的發展,中國《環境保護法》要求的“環境質量監測”義務,從“定期報告”昇級為“動態感知”。這種改變通過數據具象化,破解了傳統環境監測中的信息滯後、覆蓋不足等問題,為精準執法提供即時的、可感知的證據載體。
第二,數字技術打破各方治理壁壘,促進“協同化智治”。數字平台正在構建“政府-企業-公眾”協同網絡。例如,浙江2020年啟動的“綠源智治”是全國首個生態環境司法保護一體化協同系統。這類平台通過整合企業排污許可數據、公眾舉報信息、第三方監測報告,形成從企業排污自動預警,到監管部門快速核查,再到公眾可查詢、可監督的閉環,進而提昇環境執法精準度,加快了企業環境違法線索核實速度,讓公眾參與環境監督更高效。
第三,數字技術為維護環境權益(如知情權、損害賠償權)提供“可舉證、可救濟”的技術支撐。以往環境污染維權中,證明污染與損害的關係是個大難題。如今,檢察機關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可藉助無人機航拍,獲取污染範圍影像;使用區塊鏈存證,固定排污數據;利用算法模型,測算作物減產與污染的關聯性。這些技術有效支撐證據鏈的形成,縮短了環境損害的認定時間。其核心意義在於,把環境權益從“抽象權利”轉化為“數據化權利憑證”,強化環境權益的可救濟性。
第四,數字技術協助環境風險預判。《環境保護法》明確了“預防為主”原則,並提出要從“制度要求”轉化為“可操作的防控方案”。人工智能技術讓預測環境風險成為可能,讓“預防為主”的環保原則真正落地。
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支撐技術系統就是一個好例子。它藉助“智慧環保”項目,在重點區域建成64個空氣自動監測站,分析霧霾傳輸機理;建設“衛星遙感立體監測網絡”,以衛星遙感、大數據、物聯網智慧城市技術破解監測難題;推進“智慧城市可視化”,提昇空氣質量預報預警、污染源追蹤與應急聯動能力,為環境風險預警、信息共享、聯防聯控、協同治理提供技術支撐。
第五,以法治約束規範環境數據治理。數字技術在賦能環境權益保護的同時,也面臨數據安全、權利邊界等問題。中國生態環境部2023年出台《生態環境統計管理辦法》,為數據管理、分級保護和質量保障等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這凸顯了法律不可或缺的雙重角色:既要引導和利用好技術,也要為其應用設好邊界,確保技術助力環境權益保護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隨著環境保護與數字化深度交織,環境正義的內涵也拓展至“數字環境正義”,並提出新要求。傳統的環境正義關注的是資源分配與風險承擔的分配公平,而數字技術催生了新的權力形態,比如算法決策權(自動識別違規行為)、數據控制權(如個人碳行為數據的收集)、平台壟斷權(人工智能企業通過數據聚合消解個人數據權利)。若缺乏對這些權力的有效約束,環境不公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綜合而言,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的融合,正在將技術工具和法律規範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共同保護環境權益。一方面,數字技術提供強大支撐,持續拓寬環保空間;另一方面,生態文明為技術發展設定了生態優先的方向並明確法律的邊界。這種融合將使得未來環境權益保護從三個重要方面發生變化。
第一,治理主體上,從“人類中心”轉向“人機協同”,政府、企業、公眾依託數字平台,建構新型環境權益共同體。
第二,權益保護模式上,從“靜態確權”轉向“動態賦益”,藉助數字技術帶來的透明度,將環境權益的抽象泛化轉變為可感知、可量化、可追溯的權益保護,讓保護更精準、更實在。
第三,運作機制上,從“彼此分立”到“雙向奔赴”。通過技術革新與法律規範雙向的緊密結合,促成“數字技術賦能-法律規範適配-環境權益保護”的良性循環,進而推動“數字環境正義”的實現。(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