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曉輝
晨光初染燕山脊,我們與李鵬君踏露而行。翟翔先生早已如約靜候於秦皇島博物館階前,青衫磊落,笑意溫潤,館中工作人員亦如春風拂面。那座融合銅鼎莊重與長城雄渾的建築默然立,仿佛已在此等候了千年,只為此刻的相逢。



步入展廳,時光長河在眼前奔湧。商代乳釘紋青銅簋靜臥於柔光之下,其鑄造之精,紋飾之妙,正是《考工記》“金錫美,工冶巧”的絕佳注腳。戰國青銅劍寒芒內斂,猶帶易水風蕭的凜冽;唐代三彩陶馬釉彩斑斕,似凝固了霓裳羽衣舞動的瞬間;明代長城磚苔痕斑駁,每一道刻痕都是邊關冷月風霜的無聲訴說——此景此物,恰是前日探訪秦皇遺址、追尋魏武“東臨碣石,以觀滄海”遺蹤的悠長迴響。徐福樓船揚帆入海的場景與仿製銅馬車,更將始皇帝東巡渤海的浩蕩畫卷重現眼前。元明沉船出水的青花瓷片,如深海捧出的凝固浪花,無聲印證著這片土地作為陸海絲路交匯樞紐的千年榮光。器物雖默,卻如黃鐘大呂,震響著“鐵打山河流水朝”的滄桑箴言,唯文明根脈深植,方能於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


日近中天,翟先生引我們至山海關一隅老店,非遺渾鍋正氤氳著人間至味。白肉肥腴若脂玉,入口即化毫無膩滯;丸子香嫩似凝酪,爽滑彈牙唇齒生津。滿族飲食智慧與本地山珍海味在銅釜中奇妙交融,升騰的不僅是鮮香熱氣,更是三百年不熄的人間煙火。翟先生含笑取出一瓶新西蘭紅酒,南太平洋陽光孕育的紫紅瓊漿在杯中搖曳生姿,與渾鍋裏升騰的赤色暖霧交相輝映——舌尖上的乾坤,竟也如歷史長河,碰撞出“此心安處即吾鄉”的深長意味。張翰蓴鱸之思固然風雅,而眼前這海陸相擁、古今交匯、中西邂逅的渾鍋宴,方是紮根大地的鮮活詩篇。


餐畢,複登臨山海關中國長城博物館。此乃長城專題三大聖殿之一,明代牆磚冷峻如鑄鐵,子母火銃沉默似玄鐵,九大展廳如史詩篇章,將鋼鐵雄關的筋骨血脈層層剖現。立於城堞,朔風獵獵,耳畔似有金戈鐵馬破空而來。自秦皇鞭石築龍起,漢武揚威塞外,經宋遼金元烽火狼煙,至明清鼎革之際,吳三桂沖冠一怒開關引清騎,李闖王旌旗漫卷踏破帝王夢……多少英雄豪傑,曾在這彈丸鎖鑰之地,揮灑熱血,演盡興亡,徒留“是非成敗轉頭空”的蒼茫浩歎。忽憶去歲九月,列車穿行萬裏黃沙,終抵長城西極嘉峪關。落日熔金,傾灑於祁連雪峰之巔,將“天下第一雄關”映照得孤絕蒼勁。指尖撫過與山海關同質的冰冷牆磚,聽風沙低吟著馮勝築城、左公植柳、林公謫戍的往昔,頓覺這條巨龍首尾相連,橫亙寰宇——東起老龍頭吞波飲浪,西至嘉峪關鎮鎖狂沙,萬裏身軀便是華夏不屈的錚錚脊樑。張養浩《山坡羊》之歎穿越時空:“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邊關如鐵,興亡似水,多少鐵血悲歌、兒女情長,終被歲月長河淘盡,唯餘“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喟歎,深深烙印在每一塊沉默的城磚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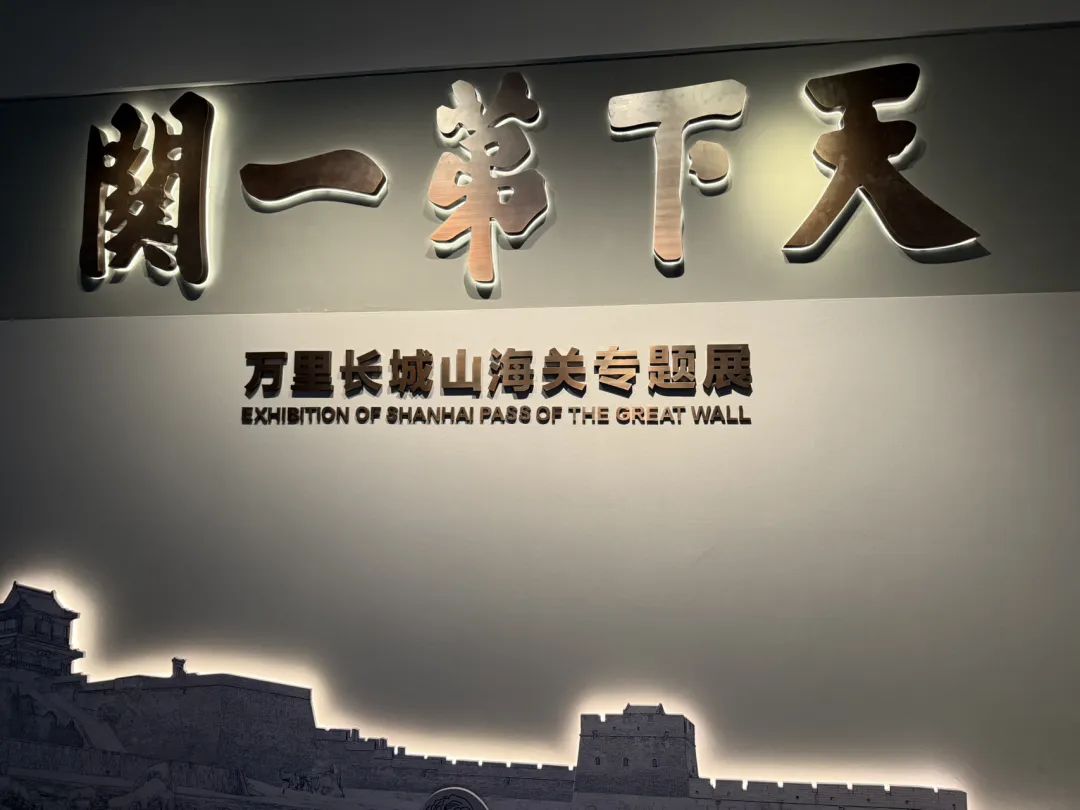

暮色漸合,執手話別。蜿蜒的城堞如巨龍隱入蒼茫暮靄,掌中渾鍋餘溫猶存,青銅簋的幽光與長城的雄影在心間交織盤桓——原來歷史並非塵封的過往,它早已化作今朝唇齒間的山海至味、眼底的萬裏河山,以及血脈中奔流不息的文化認同。這自嘉峪關風沙中一路東行,又在山海關濤聲裏尋得共鳴的感悟,最終凝結為一場跨越時空的文明盛筵。

臨別登車,回望雄關,但見渤海煙波浩渺,燕山餘脈蒼蒼,胸中塊壘與萬丈豪情交織翻湧,遂以詩記之:
《鼎簋長城宴》
翟君邀我赴雄關,山海蒼茫入鼎觴。
老龍吞海千重浪,嘉峪鎮沙萬仞霜。
簋鑒商周紋證史,城連秦漢磚書殤。
釜沸雲濤融世味,杯搖異域醉漢唐。
興亡幾度烽煙盡,唯有長風話蒼茫。
2025年8月24日於秦皇島
作者曾曉輝博士簡介:
曾曉輝博士(1968-),廣東龍川人。就讀過中國科技大學、南京大學,獲南京大學天體物理學博士學位後轉向藝術,師從雕塑泰斗潘鶴及油畫家郭紹綱教授。
2003年創立廣州新世紀藝術研究院。2009年在香港創辦《中華時報》(現為全球華人主流媒體),並陸續拓展《中華新聞通訊社》、《中華攝影報》及英國《中華時報》。聯合發起《中華電視》及世界華人流行音樂聯合會。
現任香港美術學院及香港藝術研究院院長、多所大學教授,並任粵港澳大灣區藝術聯合會主席、中華科技協會會長、世界監督學會會長等職。
學術著作豐富(藝術理論與歷史)。雕塑創作富人文關懷,作品獲全球多家美術館、藝術館典藏。積極參與國內外文旅規劃(如張家界、賀蘭山、上海及大阪世博會等)。


,俄羅斯軍方傷亡慘重。-218x150.webp)
-218x150.webp)

-218x150.jpg)
。-218x150.webp)
-218x150.webp)
-218x1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