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法靈象:藝術終極規律的理論建構與時代意義
——呂國英原創藝術論立論縱橫評析
艾 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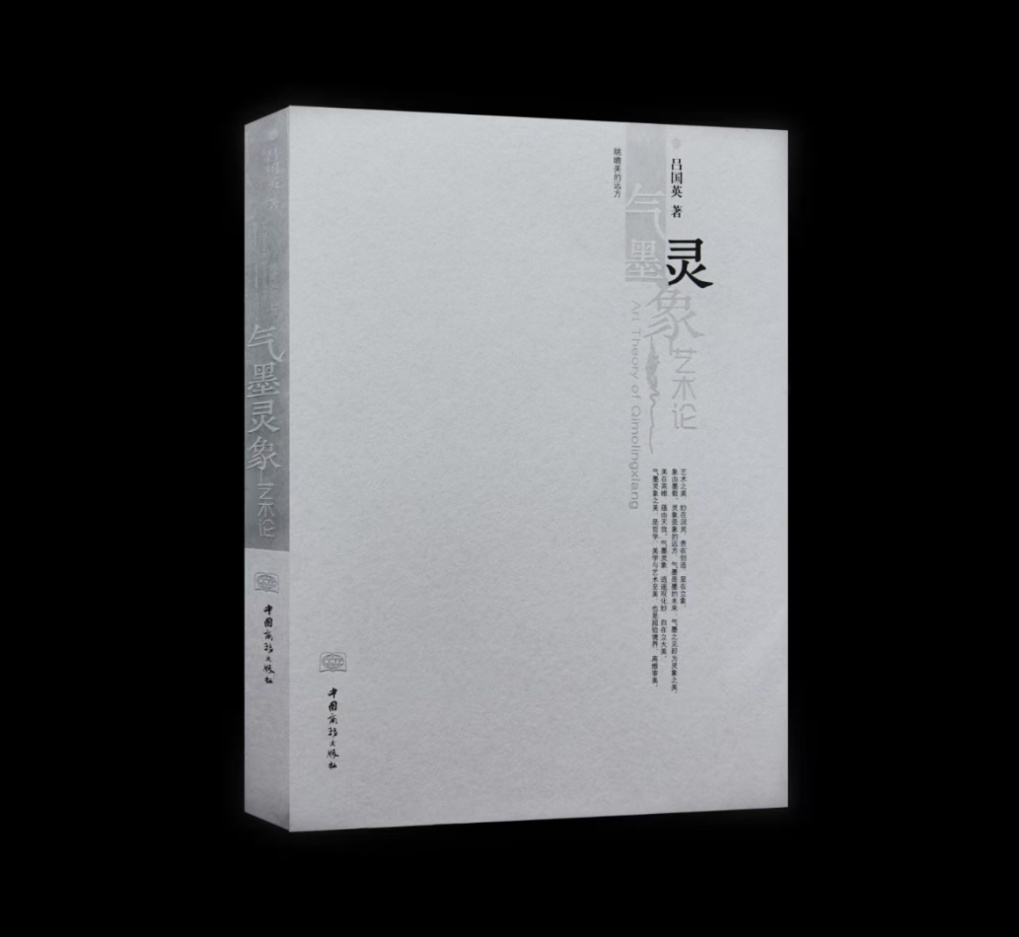
在當代藝術理論領域,呂國英先生提出的“氣墨靈象”藝術論以其恢弘的理論架構和深邃的美學洞見,構建了一個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藝術哲學體系。該理論的第四大核心命題“‘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不僅是對藝術本質的深刻詮釋,更是對當代藝術創作困境的強力回應。本文將從理論體系、歷史脈絡、哲學根基、現實批判和學術價值五個維度展開深度解讀,剖析呂國英如何通過對傳統藝術理論的創造性轉化,構建其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的理論大廈。
1 理論精髓與體系架構
“藝法靈象”作為呂國英藝術理論體系的核心命題,蘊含著對藝術本質的深刻詮釋。這一概念由“藝法”與“靈象”兩個關鍵部分組成:“藝法”之“法”並非簡單的技法規範,而是指藝術創作應遵循的根本法則與至高境界,是“藝術之道,也是藝術之遵循、之範習,還是藝術之引領、之效仿”;而“靈象”之“靈”則被賦予本體論意義,是“真之本、善之源、美之魂、愛之緣”,是“覺之根、悟之原、慧之初、明之淵”,其核心論斷在於“無‘靈’則無美,入‘靈’(境界)方至美”。在呂國英的理論體系中,“靈象”被視為藝術之象演進的最高形態與終極目標——“靈象從具象走來,經意象、抽象、真象(具象、意象、抽象三象合一),最終進入靈象”。
“氣墨靈象”理論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由八個相互關聯的立論組成整體框架:《逸形入靈 大藝立象》與《如氣化墨 載靈承象》作為分論篇,分別奠定“靈象”與“氣墨”的概念基礎;《氣墨繪畫 靈象藝術》作為合論篇,將二者融合為“氣墨靈象”這一新藝術形式;《藝法靈象 至美審美》作為綜論篇,則系統闡釋“藝法靈象揭示藝術本質規律”這一核心命題;其餘四篇則從不同維度完善理論體系。這一建構過程展現出呂國英對藝術理論體系化的自覺追求。
在呂國英的理論視野中,藝術的歷史演進呈現出清晰的階段性規律:“藝法具象是藝術的相對規律,藝法意象、抽象是更高一級的藝術相對規律,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遠方規律,一定意義上也是藝術終極規律”。他創造性地將中國藝術史中筆墨與象態的演進關係概括為五個階段:
表:藝術之象與筆墨形態的演進階段
演進階段 筆墨形態 藝術之象 核心特徵
第一階段 線墨 具象 寫實再現,形似為上
第二階段 意墨 意象 心物交融,得意忘形
第三階段 潑墨 抽象 離形得似,形式探索
第四階段 樸墨 真象 三象合一,返璞歸真
第五階段 氣墨 靈象 天人合一,超驗境界
資料來源:根據《“氣墨靈象”藝術論》整理
呂國英提出的“氣墨·靈象互為形式內容”論,構成其理論體系的辯證核心。在他看來,“氣墨”與“靈象”是同一藝術本體的兩面:“氣墨是靈象的筆墨,靈像是筆墨的氣墨,無氣墨即無靈象,無靈象也必無氣墨,兩者如影相隨、不可割裂,即互為形式,亦互為內容”。這種辯證關係突破了傳統藝術理論中內容與形式的二元對立,將藝術推向形質一體的至高境界。
“至美審美”作為“藝法靈象”的必然結果,被呂國英賦予超驗性內涵。他認為至美是“大美,也是極致之美”,與中國傳統文論的“大美”“大象”、西方哲學的“理式之美”異曲同工。在美學的層級劃分中,他特別強調“創造美”的價值——這是美的“無中生有”,體現為“想像美、理想美、發現美、獨創美、嶄新美,是美的最高形態”,其根本價值在於“原創、惟一、不可重複”。這種對創造性的極致追求,使“氣墨靈象”理論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和前瞻性。
2 歷史脈絡與理論突破
呂國英“藝法靈象”理論的建構建立在對中國藝術史,特別是筆墨論爭史的深刻反思之上。他系統梳理了從董其昌、陳繼儒到清“四王”的“筆墨至上論”,指出這種觀念如何演變為“作畫第一論筆墨”的教條;同時分析了以石濤為代表的“筆墨反思論”,特別強調其“筆墨當隨時代”的革新精神;對於現當代傅抱石、石魯、吳冠中等人的“筆墨憂患論”與“筆墨無用論”,呂國英也給予辯證審視,認為這些觀點雖是對筆墨至上論的反撥,卻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理論困境。
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三次重大筆墨論爭——20世紀初的“中國畫改良論”論爭、1980年代的“中國畫窮途末路論”論爭、1990年代的“筆墨等於零”與“守住中國畫底線”論戰——在呂國英的理論視野中被視為同一問題的歷史變奏。他認為這些論爭“基本是就筆墨論筆墨,皆無最終或建設性結論,甚至成為一種‘公婆’論、‘混’論”,其根本癥結在於“沒有進入理論層面,沒有提出關於筆墨之新觀點、新立論”。這種理論困境直接導致了筆墨實踐的僵化,表現為“陳、俗、髒、假、亂、死”六大問題,其中“死是問題的根本”,根源在於“筆墨的程式化、僵化、概念化”。
呂國英對“西畫東漸”歷史現象的解讀,揭示了20世紀中國藝術的文化心理困境。他指出,徐悲鴻、林風眠、吳冠中等人的留學潮與西方藝術理論的引入,本質上是“由於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藝術漸以頹敗,國民尤其是藝術中人,缺乏甚至沒有了文化與藝術自信”的表現。這種文化自卑心理導致藝術界長期陷入“以洋為美、以洋為尊、唯洋是從”的誤區,甚至出現“去中國化”“去歷史化”“去主流化”的極端傾向。
“藝法靈象”理論的提出,正是對上述歷史困境的根本性超越。呂國英通過重構藝術史演進邏輯,將“靈象”確立為藝術發展的必然方向與終極目標,從而跳出了傳統筆墨論爭的窠臼。他提出:“靈像是最高層級的藝術之象,始終是象的遠方;至美是美的最高層級的審美體驗,始終是美的未來。靈象無恒,至美無境。”這種歷史觀既尊重藝術發展的內在連續性,又為其開闢了永恆的開放空間。
在方法論層面,呂國英對筆墨載象論的創造性發展尤為值得關注。他提出:“不同的筆墨語言表達與體現不同的藝術之象,於是就有了線墨繪畫·具象藝術與意墨繪畫·意象藝術之別,也有了潑墨繪畫·抽象藝術與樸墨繪畫·真象藝術之異,也自然有氣墨繪畫·靈象藝術之論。”這一理論模型不僅清晰勾勒出中國藝術的歷史演進軌跡,也為未來藝術發展指明了方向——氣墨承載靈象的藝術形式將成為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
3 哲學根基與美學融合
呂國英“氣墨靈象”理論體系的建構,植根於深厚的東西方哲學土壤,展現出恢弘的跨文化視野。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他創造性地轉化了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觀,將其與藝術規律相貫通:“雖然,藝術規律不能與自然、社會規律簡單相類比,但本質性、根本性規律的終極指向性是相同的、毋容置疑的。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根本性規律。”這種將藝術規律與宇宙規律相貫通的思維方式,賦予其理論以形而上的哲學高度。
莊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哲學境界,在呂國英理論中被轉化為“靈象”的核心內涵。他認為靈像是“多層次天人合一的正大象態、悟美之境、藝術大美”,是“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象”。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需要通過藝術家“自我救贖”式的精神修煉才能達到,體現了中國哲學中“內聖外王”的修養傳統在藝術領域的創造性應用。
在美學層面,呂國英的理論展現出融合東西方美學的宏闊視野。他將宗白華的“靈境說”、本雅明的“靈暈說”與顧愷之的“通靈說”、石濤的“山川效靈論”相貫通,共同構建“靈象”的美學內涵。在闡釋“至美審美”時,他既援引中國傳統文論的“大美”“大象”“象外之象”等概念,又將其與西方古希臘哲學的“理式之美”相呼應,體現出跨越文化疆界的理論包容性。
呂國英對美與審美關係的哲學思考,構成了其理論的認識論基礎。他提出:“美與審美,由理念到存在,既為‘心嚮往之’,亦為‘審’之‘判斷’。‘至美’之審美,正是極致之美的心性美,也是終極之美的判斷美。”這一觀點既吸收了康德“審美判斷力”思想,又融匯了中國傳統美學中的心性論,形成了獨特的美學認知框架。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呂國英對創造美的本體論提升。在分析美學之美的構成時,他特別強調:“創造美屬美的‘無中生有’,突出體現為想像美、理想美、發現美、獨創美、嶄新美,是美的最高形態,核心在於藝術創造,原創、惟一、不可重複是其根本價值所在。”這一觀點將藝術創造提升到宇宙創生的高度,與《周易》“生生之謂易”的創生哲學遙相呼應,展現出深邃的哲學視野。
呂國英還從文字學角度對藝術本質進行了獨特闡釋。他分析“藝”字原為“埶”,象形“將兩粒種子置於土壤之間”,後演變為“藝”(藝),寓意“上有奇花異草,下有行雲流水,中為生計無虞”;而“術”之原字“術”則被解讀為“十八般武藝一點通”,寬闊大道有“術”則行。基於此,他提出:“藝為美,術為技,藝術合一,就是盡美之美矗審美立象之道,不擇手段行(審美立象)技術之通。”這種文字學闡釋賦予其理論深厚的文化底蘊。
4 現實批判與亂象診療
呂國英構建“藝法靈象”理論絕非純粹的學術思辨,而是針對當代藝術亂象的深刻診療方案。他以犀利的批判眼光,系統梳理了當下藝術領域的八大亂象,直指藝術創作生態的深層病症——
創作異化:“抄襲模仿、千篇一律,複製性生產、速食式消費”,表現為“既抄經典,也抄現代,既仿古人,也仿今人,既複製名家,也重複自己”。
審美墮落:“獵奇逐豔、低俗諂媚,善惡不辨、以醜為美”,表現為“調侃崇高、扭曲經典,糊塗亂抹、粗製濫造,甚至渲染陰暗,製造文化與藝術‘垃圾’”。
創新迷失:“追求形式、缺少內容、蔑視傳統、遠離現實”,表現為“重形式包裝、缺內容支撐,追求奢華、炫富擺闊,甚至熱衷於‘為藝術而藝術’”。
心態浮躁:“心緒浮華、精神迷離,甚至投機取巧、沽名釣譽”。
文化自卑:“以洋為美、以洋為尊、唯洋是從,把獲得國外獎項作為最高追求,甚至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中國化’‘去歷史化’‘去主流化’”。
圈子固化:“江湖氣、‘圈子’化、近親繁殖、‘門派’思維”,表現為“師傅帶徒弟式傳承、家族作坊式生產,熱衷於‘抱團取暖’、進‘圈’為榮”。
市場扭曲:“以‘職’定價,以‘銜’論價”,表現為“自我炒作、聯手炒作、刻意運作,‘假拍’‘拍假’,‘守株待兔’”。
批評失語:“庸俗吹捧、阿諛奉承”,表現為“無底線拔高,無標準叫好,仿佛隨處有‘大家’、人人是‘大師’”。
呂國英尖銳指出,這些亂象的根源在於藝術界對終極藝術規律的集體迷失。藝術市場化的衝擊導致“藝術業界乃至學界的心性浮躁,並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反向迴圈,愈演愈烈”。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理論領域的“混論”盛行——所謂“混論”,即“混亂之論,就是沒有共識、缺乏本質性見地之論,就是自言自語、隨性所論”。他痛陳當下藝術理論研究的困境:“借搜索引擎以關鍵字搜索,顯示出的數字結果竟達百萬級。然而,令人感慨與唏噓、尷尬又無奈的是,打開這些網頁與論章,搜尋相關論證與解讀,幾乎篇篇缺‘本’解,章章少‘質’根。”
面對如此亂象,呂國英認為“藝法靈象”理論提供了根本解決方案。這一方案包含三個層次的矯治邏輯——
本體論矯治:以“靈象”重建藝術至高標準,將藝術從技術層面提升至靈性境界,重塑藝術創作的精神高度;
方法論革新:以“氣墨”突破傳統筆墨桎梏,強調“如氣化墨”的創造性轉化,為藝術表達開闢新境;
價值論重鑄:以“至美審美”對抗低俗趣味,通過創造美的超驗體驗重建藝術的神聖價值。
呂國英特別強調藝術家的精神修養是實踐“藝法靈象”的關鍵前提。他提出“高學大德方立氣墨靈象華章”的命題,認為只有具備“高學”(深厚學養)與“大德”(崇高品德)的藝術家,才能進入氣墨靈象的創作境界。這一觀點繼承了中國傳統“文以載道”“藝由德崇”的精神傳統,為抵制藝術界的浮躁風氣提供了人格典範。
5 學術價值與理論超越
呂國英“氣墨靈象”理論體系的建構,在當代中國藝術理論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其學術價值首先體現為理論體系的本土性建構。在長期受西方藝術理論主導的中國當代藝術學界,呂國英立足中國傳統美學範疇(如筆墨、氣象、意境等),構建起具有鮮明中國氣派的藝術理論體系。正如藝術評論家、學者劉常所評價的:“筆墨論、氣象說,皆為獨具中國氣派的藝術理論範疇,由此為起點而構建起的理論大廈,必然是對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的繼承與發揚。”這種理論建構對於增強中國藝術理論的主體性與話語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其次,該理論實現了藝術史觀的重構。呂國英創造性地提出“五墨五象”的藝術史演進模型(線墨·具象→意墨·意象→潑墨·抽象→樸墨·真象→氣墨·靈象),為理解中國藝術發展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這一模型既尊重藝術史實,又具有理論前瞻性,將藝術史解讀從簡單的風格演變提升到哲學高度,展現出宏闊的歷史視野。
第三,該理論在藝術批評標準上取得重大突破。針對藝術批評領域長期存在的標準混亂問題,呂國英提出“藝法靈象就是藝術的根本性規律”的論斷,為藝術評價提供了明確的價值座標。基於此,他進一步提出藝術作品“五尚”(尚絕、尚新、尚進、尚融、尚極)與藝術家“五崇”(崇學、崇德、崇靜、崇變、崇論)的批評標準,以及創作者“五忌”(忌盲、忌混、忌怨、忌欲、忌偽)與接受者“五忌”(忌物癖、忌追風、忌固舊、忌媚俗、忌盲從)的警示,構建了完整的藝術評價體系。
呂國英的理論貢獻還在於其對藝術終極價值的重估。他突破傳統美學對“美”的有限理解,提出“美是‘氣墨靈象’”的命題,認為“氣墨靈象表現與通達靈性境界,是超越藝術形態,也是超越藝術之美,呈現藝術極致,體現至美審美”。這一觀點將藝術價值從形式層面提升到精神超越層面,與當代社會對精神價值的深切需求形成呼應。
當然,任何理論體系都有其反思空間。呂國英“氣墨靈象”理論可能引發的學術討論集中在三個維度——
理論適用邊界問題:源自中國書畫傳統的“氣墨靈象”理論,是否適用於解釋其他藝術門類(如音樂、戲劇、電影等)的創作規律?
靈象體驗的可驗證性:作為超驗境界的“靈象”如何在藝術批評中建立可操作的評判標準?
傳統與創新的張力:在強調突破傳統的同時,如何避免陷入另一種形式的歷史虛無主義?
這些問題的可能存在並不減損呂國英理論的價值,反而為其發展提供了開放空間。正如劉常所指出:“理論對現實的解釋終難網羅萬象…理論的最終價值應體現在對所論現象作出相對而言最為合理的解釋、理解與預期,而非對所有現象包舉囊括。”在這一意義上,“氣墨靈象”理論以其宏大的體系建構和深刻的現實關懷,已經實現了對傳統藝術理論的重要超越。
結語:走向靈象的藝術未來
呂國英先生提出的“氣墨靈象”藝術論,以其恢弘的理論架構和深刻的美學洞見,為當代中國藝術理論樹立了新的思想座標。這一理論體系不僅完成了對中國傳統藝術思想的創造性轉化,更對當代藝術亂象提出了切中要害的診斷方案。其核心命題“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既是對藝術本質的深刻詮釋,也是對藝術未來的方向指引。
在藝術創作層面,“氣墨靈象”理論為突破傳統筆墨桎梏、實現藝術語言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在藝術批評層面,該理論構建的價值標準體系為鑒別藝術高下、抵制低俗趣味確立了明確準則;在藝術教育層面,“高學大德”的創作主體論為藝術人才培養指明了精神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自信建設的時代背景下,這一具有鮮明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為構建中國藝術話語權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
“靈象無恒,至美無境”——呂國英用這八個字概括了藝術的永恆追求。在藝術創作日趨商業化、膚淺化的今天,“氣墨靈象”理論所彰顯的精神高度和美學理想,恰如一劑喚醒藝術本真的良方。它提醒我們,真正的藝術永遠指向人類精神的至高處,那是超越時空的靈性之境,是藝術永恆的“遠方”和“未來”。走向靈象的藝術之路,就是回歸藝術本質的超越之旅。
(論文原文載:《解放軍報》長征副刊、《文藝報》《人民政協報》學術家園、《“氣墨靈象”藝術論》·中國商務出版社;《粵海風》《中華時報》理論連載等)
2025.04.27·北京
附
呂國英 簡介
呂國英,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家,文化學者、詩人、狂草書法家,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中華時報藝術總監,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創立“氣墨靈象”美學新理論,建構“哲慧”新詩派,提出“書象·靈草”新命題,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專著多部、原創學術論文多篇,撰寫哲慧詩章兩千餘首。
主要著作:《“氣墨靈象”藝術論》《大藝立三極》《未來藝術之路》《呂國英哲慧詩章》《CHINA奇人》《陶藝狂人》《神雕》《國學千載“牛”縱橫》《中國牛文化千字文》《新聞“內幕”》《藝術,從“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論:“靈象”是“象”的遠方;“氣墨”是“墨”的未來;“氣墨”“靈象”形質一體、互為形式內容;“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美是“氣墨靈象”;“氣墨靈象”超驗之美;“書象”由“象”;書美“通象”;“靈草”是狂草的遠方;詩貴哲慧潤靈悟。






